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ƪС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70ƪ���ߵĶ�ƪС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ƪ��֮ǰ�汾�ġ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
�ҽ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ʼ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Ϻ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ȿ����ϰl(f��)�ˎ�ƪ�ж�ƪС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j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ؓ(f��)؟(z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Ї��ˑ������˵ĕ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Ϳ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Ќ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ЌW(xu��)δ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“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ɲ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߾��귵�ر�������Ȣ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һ�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e�˵ĺ���һ�ӿɐ������@�ӵĽ�(j��ng)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κ��Ї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Ҿ���ô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c(di��n)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Ҍ�Щ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Uӡ�����ĵط������QһЩ�X���N�a(b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c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㹤��ľ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�ʲô��ͬ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
�{�� ���� ϴ�� ѩɽ ����
�˕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p
���R �� ���� ���I(y��) ����
ҹ· ���� ��ـ ���� ���T
��Ь ��Ҋ ɽ�� ���L
�s ɫ
�f�� 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 ��� ��ˮ
��θ Ұ�i ѝ�� ��ä �Y(ji��)��
ƽ�� ��� ���L(f��ng) ���� ���b
��Փ ��� �^�� ɫ�� ��
ج�� �ؑ� �a(b��)�w ���� �X��
Сȸ �լ �Ϸ� ��Ƭ ����
�v�� ���� �Ҿ�
�� ��
�ʌmɢ� �����c(di��n)�� ���� ��(ji��)��
���� ɵ�� �P� �䘶 ���D(zhu��n)
��· ï�� 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
�� ��
��(d��ng)�ºÿ��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ʮ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˪qԥҪ��Ҫ��һ���f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ǁ���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Äe�˵K�������fЩ��Ԓ��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^���x�߱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“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”����“�˕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p”������“�sɫ”���һ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r(sh��)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X˯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l�Ýh����߀ӛ�î�(d��ng)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С�z�ڽY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[���[����ҹ�����ڶ�����߀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ϱ�D���ܵ����Ϫ�(d��)�Դ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һҹ�������˻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߀�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ϵ��˶�������Ц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g��)�z�^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Ц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@�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
���p��ʢ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Ȼ��ʢ����Ԫ?d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Ԫ�(d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ĕ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ÿ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q�Ժ��ٿ�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п�ĕ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̎�ĕ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Ǡ�B(t��i)����¶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ĕr(sh��)��(d��ng)Ȼ����¶�����p�Ġ�B(t��i)����B(t��i)һ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ԬF(xi��n)�ځ����Ǖ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¹P����Խ��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(t��i)ԭ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ؓ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p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X̎�������njW(xu��)��ǻ����ˇǻ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ӑ������ӑ��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ǻ�������Ԟ��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ЌW(xu��)�r(sh��)��“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x”���X���@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r(sh��)��ʢ�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����²�ԓ�@�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ng)ԓ���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̵��ֲ�Ը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h(yu��n)Ҫ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r(sh��)��Ҋ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̭�ĕ����Ƕ������Ž����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Ǜ]��һ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c�ҵ�ͬ�g�˵��Ļ���(g��u)�ɲ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(g��u)�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(d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͕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ˡ��Ҿ��ǎ����@�N�ְW��й��Ġ�B(t��i)ȥ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ȥɽ���㱱����ͬȥ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С�W(xu��)ͬ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t��һ��ȥ�r(sh��)�J(r��n)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ɂ�(g��)���ѬF(xi��n)�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гɾ�������ɣ�ɺӸ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ȁ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к͎���Ů���е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ЌW(xu��)���ݼ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Ё��\(y��n)�ĸ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ݺ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_ɽ��ǰ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“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����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˲��ɰ����ᭇ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ᭇ߀�Ѓ����Ǵ�”��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˼�����õ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
�^֮ȥ��(n��i)�ɹź�ؐ���˰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ͬȥ��߀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@��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ϼt�h(y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õ�ʮ�킀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֬���^֮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R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ǂ�(g��)�v���F�v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H��һ�Ώĸ������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ð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һĘ���֑���ϲ����
��ȥ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˺Õ�����
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ֹ��Ƶ�“�P(gu��n)��”��ӹܔU(ku��)��C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䌍(sh��)�P(gu��n)�˵�“�P(gu��n)”�����ǝM������չϠ��ӵĝh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U(ku��)��C(j��)�����Ӳ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Ҋ�^“�ʼ�ţ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ʼ��˳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Խ�ǻʼ�Խ���N�ʼҵĽ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늹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ɫ��õĽ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յ��ഺͬ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뮔(d��ng)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ʮ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~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Ź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т���m(x��)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y��n)鸸�H�Ć��}�����B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ˇУ��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ȥ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֏�(f��)�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ܶ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 ��“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ÿ��߀����ɽ�ɻ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̽�H�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܇�M(j��n)վ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һ·�u��һ���N�ô�܇݆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δ��R“�������ѵ�”�����ܶ���]�� 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ë�ɖ|�^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游�H���c(di��n)�|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ԺԺ�L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Ҋ�����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ɮ�붨�����f�Ǿ�ί�������ڴ��^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˵Ļ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ˆ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˲�������Ц���ۜI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ĕ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Ҧ���^“���ˎ�”��ץ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漤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Ѽ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팑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_�ČW(xu��)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治���S���ε�׃����׃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(x��)�T���̖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ʼ�ĕ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Ė|��һ����ӛ��ס�Ė|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ǏUԒ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UԒ���ɽ�(j��ng)�(y��n)�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ЏUԒ����̎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Ϣ�f������֪�R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o(j��)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ҵĽ�(j��ng)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ഺ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ǐ����@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��ഺ��äĿ������äĿ�Đ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ܵİl(f��)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Ж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؈�l(f��)��r(sh��)�Ĕ��_�����ܔ_�߽ԕ���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“֪���ČW(xu��)”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ng)ԓ���ഺ�ČW(xu��)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Ҳֻ��â�˵ġ�Ұ�¡�һ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F(xi��n)�ڻ��^ȥ�����^“֪���ČW(xu��)”�������ǟo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ഺ����߅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ؿ���һ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һ·�����oһƪ�c�ഺ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ֻ��Щ���p�r(sh��)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P(gu��n)ϵ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o�P(gu��n)���ഺ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С�f������“֪��С�f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ഺС�f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ˡ��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˷��һƪ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}Ŀ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ഺ�y����߀���ڌ���Ҫ���쵽�ܸ��X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Ǹ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ŕ��Ǹ��X��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f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^ƤҪӲһЩ����Ӳ���^Ƥ���܌�һЩ�F(xi��n)�ڿ���Ę�t�Ė|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һ�žŰ����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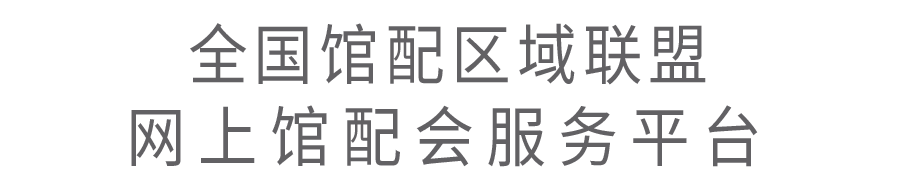
 �������]
�������] �����]
�����]